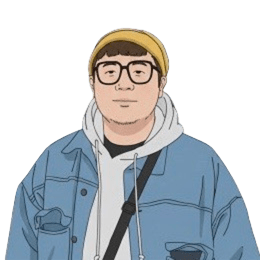觀點專欄|人生的開始是偶然,結束能不能成為選擇?
出生是偶然,死亡卻成了被剝奪的選擇。當活著被定義成一種責任,而不是一種自由時,人生究竟還剩下多少屬於自己的主權?

人的出生無法自己決定,但連死亡我都得活在他人期待裡嗎?安樂死這議題,常常沒幾年就會被拿出來討論,討論的時機大多時候,都是在於有相關新聞的發生時,大家才會想起,其實「不能決定自己死亡」是痛苦的。
對於出生,活在這世界上已經不是我能控制的,但至少我能控制自己離開的時間吧?但目前台灣的法規不允許我們這麼做,就包含自己的親人似乎也是如此。

出生的偶然,生命的必然
要聊死亡前,我們應該要先聊出生。我們誰都沒有選擇出生的權利,無論是投胎到富裕的家庭,或是背負著貧窮與疾病,常常被網友們嘲笑的人生「地獄開局」,這一切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。
從某種角度來看,這就是「宿命」的起點。然而社會卻在這個偶然之上,給了我們一個必然的要求,既然活著了,就必須盡力「好好活下去」。有人說:
「人生最不公平的起跑點,就是出生;而最公平的終點線,就是死亡。」
但諷刺的是,當我們抵達終點時,卻仍然沒有選擇的自由。我必須要等著我身體有疾病,或是意外的到來,我才能正大光明地迎接「死亡」。
老實說,這真的很不公平。

活著的重量,不只是生理上的延續
延續壽命在現代醫療的協助下並不難,但如果生活只剩下疼痛、病床與機器維持,那樣的「活著」是否還算真正的生命?
我奶奶八十多歲,有將近七年的時間她都躺在床上,前一兩年還能夠講話,但時間一拉長,她誰都認不出來。她活著的目的,似乎只成為照三餐吃飯,以及正常大小便而已,她的生活已毫無意義,但我們卻不能讓她體面的離開。
對病人而言,生理功能的延長,有時只是精神折磨的加劇。對家屬而言,看著至親受苦,卻又無法違背社會「孝順」的期待,內心更是煎熬。看著我爸照顧奶奶,他心裡肯定有許多不能對我們說的話,但他只能一直照顧著奶奶,因為似乎只剩這一條路可以選擇。
台灣曾有位 ALS(漸凍人)病友受訪時說過一句話:
「醫療讓我的心臟還在跳,但我的靈魂早已被困在身體裡。」
這句話,或許比任何醫學數據都更能展現「生命質量」與「生理延續」的差異。也因此,當人失去了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,便更渴望能擁有選擇結束的權利。

死亡自主權的爭議與現實
所以我支持支持安樂死應該要存在,無論什麼方式。
我一直都很納悶,為什麼「安樂死」是需要被討論的。反對者說生命屬於神明,不應被人為決定;支持者則認為,若活著的每一刻都充滿折磨,那麼死亡不應只是悲劇,也可以是解脫。這場辯論從宗教、法律延伸到倫理,每一方都有無法輕易否定的理由。
荷蘭是全球第一個通過安樂死法案的國家,一位 80 歲的阿茲海默症患者在簽下「提前醫療意願書」後,選擇在家人陪伴中離開。她的兒子在記者會上說:
「母親最後的笑容,是她一生中最自在的一次。」
有機會能夠與愛的人好好道別,我有能力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度過最後的日子,為什麼這件事情是需要被同意的?那些躺在病床上的患者們,對自己的身體無能為力,還得在家人的期待下活久一點,但他們真的有「活」著嗎?
讓自己擁有對生命最後的選擇權,不是一件很基本的事情嗎?

選擇的自由,還是制度的缺席?
當一個社會無法正視死亡議題,最終就會把個人的選擇推給家庭、醫院,甚至是命運本身。這樣的推託,表面上保護了「生命」的神聖,但背後卻讓許多人被迫在痛苦裡耗盡最後一絲尊嚴。
若出生已經無法自己決定,那死亡至少應該成為我們能握在手裡的選項。
我不確定制度上,為什麼會逼迫生病的人不能離開,家人得花大把的金錢與時間,維持生病的人的生命,這樣制式的「延續生命」到底是誰贏了?老實說,我心中真的沒有一個答案。
在台灣現在老齡化越來越嚴重的情況,未來年輕人要照顧家中的長輩只會越來越多。若我是長輩,我肯定不希望自己會影響到兒女。更直白的說,我不希望成為任何人的累贅。
但在安樂死能合法之前,我似乎沒有能夠選擇的自由。

學會離開,也學會活著
出生與死亡,都是人生無法迴避的兩端。無法選擇出生是宿命,但不能選擇死亡卻是一種人為限制。
當社會要求我們「好好活下去」時,是否也該給予我們「好好離開」的權利?如果生命的價值在於尊嚴,那麼最後一刻的自主,才是真正屬於每個人的自由。